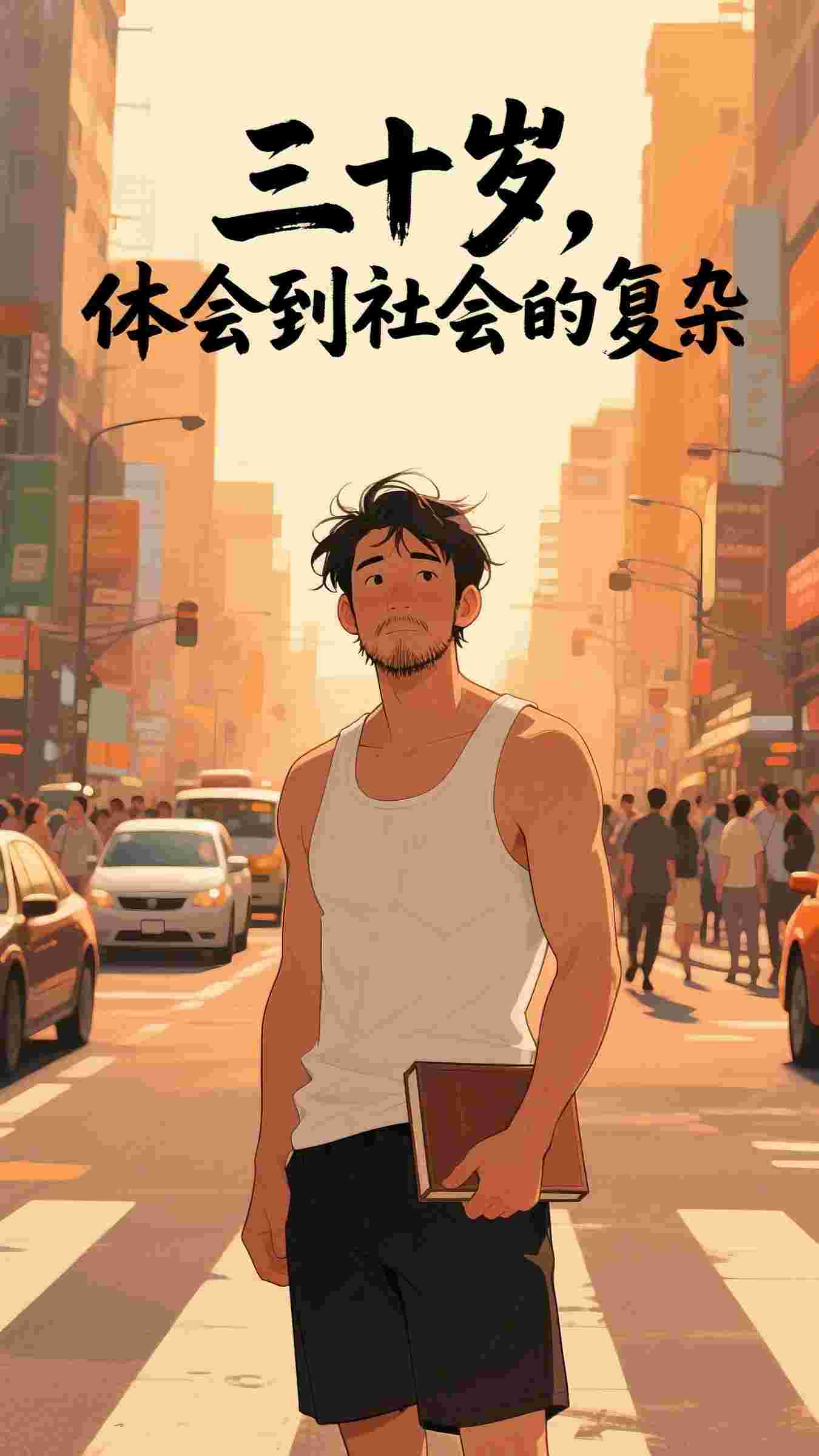- 读书简介
小说《杀人减功德这仙还修个锤子:结局+番外》,现已完本,主角是陈默王五,由作者“东北马哥”书写完成,文章简述:整套动作在无数次的操练下,已经化为本能。硝烟和血腥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,但指挥官冰冷的声音,是他们唯一的准绳。第二排的士兵踏前一步,将沉重的火铳架在临时搭建的木架上,重复着刚才那毁灭性的动作。“轰!轰!轰!”又是一道死亡的火墙...
第14章
山谷之上,死寂被陈默冷漠的声音划破。
“第二排,上前。”
“举铳。”
“开火!”
没有丝毫的迟疑,第一排的士兵冷静地退后,开始用随身的通条清理铳管,熟练地从腰间的牛皮子弹盒里取出纸壳定装弹,咬开,倒入火药,塞入铅弹和通条上的布片,夯实。整套动作在无数次的操练下,已经化为本能。硝烟和血腥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,但指挥官冰冷的声音,是他们唯一的准绳。
第二排的士兵踏前一步,将沉重的火铳架在临时搭建的木架上,重复着刚才那毁灭性的动作。
“轰!轰!轰!”
又是一道死亡的火墙。
刚刚从第一轮打击的懵懂中惊醒,试图在军官的呵斥下重整队形的崔家甲士,再一次被迎面而来的钢铁风暴撕碎。这一次,打击的距离更近,效果也更加恐怖。
一个百夫长,刚刚举起长刀,试图将一个转身欲逃的士兵砍倒,以维持军纪,他的胸甲上就猛地绽开一个拳头大的窟窿,整个人像被攻城锤砸中,向后倒飞出去,连带着撞倒了身后的两名同袍。
这一次,他们听到了同伴那不似人声的惨叫,看到了在空中飞溅的碎肉和内脏,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连反抗机会都没有的,纯粹的绝望。
恐慌,如同决堤的洪水,瞬间在密集的阵型中蔓延开来。
“魔鬼!这是妖法!”
“是天雷!土地爷发怒了!”
“跑啊!快跑!”
所谓的精锐,所谓的百战之师,在一种完全超出他们理解范畴的武器面前,彻底崩溃了。纪律荡然无存,勇气化为乌有。他们丢掉笨重的盾牌,扔掉无用的长刀,哭喊着,尖叫着,转身就往后跑。
然而,这狭窄的谷道,来时是进军的壁垒,退时,便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。
前面的人想跑,后面不明所以的人,在后方军官的驱赶下,还想往前挤。两股人流瞬间对冲,人撞人,人踩人,整个谷道乱成一锅滚烫的沸粥。摔倒的人,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,就会被无数双脚踩成肉泥。
“第三排!自由射击!清理谷口!”
陈默的命令,如同死神的判决,冰冷而不带一丝情感。
“轰!”
“轰!”
“轰!”
零星但更加致命的枪声,开始在山谷中不断回响。每一次轰鸣,都像死神的点名,精准地带走一个试图组织抵抗的军官,或是一个跑得最快的逃兵。神机营的士兵们,眼中已经没有了初次杀人时的不适与慌乱,取而代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专注。他们不再去想对面的是不是活生生的人,他们眼中只有目标,只有准星,只有扣动扳机的动作。
他们,已经从一群拿起武器的农民,蜕变成了陈默手中的工具,一台高效而冷酷的杀戮机器。
远处的崔明远,如坠冰窟。他脸上的豪情万丈早已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苍白与恐惧。他看着自己的军队,那支让他引以为傲,足以横行河间府的精锐,在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,就被那恐怖的雷鸣与火焰,打得土崩瓦解,全线溃败。
他想不明白。
这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剧情不应该是他带着大军,如秋风扫落叶般将青阳县踏为平地,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陈默,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踩在脚下吗?
为什么会这样?
“公子!快走!顶不住了!再不走就来不及了!”身边的亲卫队长,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,此刻声音里也带上了哭腔,他一把拉住崔明远的马缰,拼命地想要调转马头。
“走?”崔明远喃喃自语,随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起来,“往哪儿走!本公子不走!给我顶住!杀了他们!给我冲上去杀了他们!”
他拔出腰间那柄镶金嵌玉的佩剑,歇斯底里地嘶吼着,可他的声音,被淹没在山谷中那巨大的轰鸣与惨叫里,显得如此微不足道,甚至有些滑稽。
没有人听他的。
就连他最忠心的亲卫,看向山谷的眼神里,也充满了无法遏制的恐惧。他们护着状若疯癫的崔明远,强行调转马头,混在溃兵之中,狼狈地向后逃窜。
就在这时,山谷两侧,忽然响起了震天的喊杀声!
“杀啊!保卫青阳!”
“为陈大人报效死力!”
无数衣衫褴褛,但眼神决绝的乡勇和矿工,在李疤子等人的带领下,从山林中冲了出来。他们手里拿着的,是矿镐,是锄头,是削尖了的木棍,甚至还有粪叉。
他们没有傻乎乎地去冲击那些还穿着铁甲的崔家溃兵,那无异于送死。他们像狼群一样,缀在溃兵的两翼和后方,将早已准备好的石头、滚木,狠狠地砸向那些负责押运粮草、装备最差的杂兵。
李疤子赤着上身,虬结的肌肉在阳光下泛着油光。他抡着那柄陪伴他多年的大铁锤,怒吼着冲进一群杂兵之中。一锤下去,一个惊慌失措的杂兵连人带头盔,被砸得脑浆迸裂,红的白的溅了一地。
他咆哮着,像一头被激怒的熊,“狗娘养的!还敢来抢你爷爷的地盘!”
溃败的洪流,被这突如其来的侧翼攻击,搅得更加混乱。而当他们惊慌失措地逃回之前经过的谷口时,迎接他们的,是“土地爷”王老根,为他们精心准备的“厚礼”。
“哎哟!”一个跑在最前面的马匪,连人带马,掉进了一个伪装得天衣无缝的大坑里,坑底,是密密麻麻削尖了的竹竿。战马的惨嘶和人的惨叫混在一起,听得人头皮发麻。
“我的脚!”一个崔家士兵,被一根藏在草丛里不起眼的绊马索,狠狠地绊倒在地,还没等他爬起来,就被身后蜂拥而至的同伴,活活踩进了泥土里。
王老根扛着锄头,站在一处高地上,看着自己的“杰作”,得意地叉着腰,对身边一个负责记录的村民吹嘘:“看见没?这就叫‘神机妙算’!你得记清楚了,这不叫陷阱,这叫‘土地爷神罚之阵’!土地爷我略施小计,就够这帮龟孙子喝一壶的!记下来,都记下来!以后写进咱们青阳县的县志里去!”
旁边的乡勇,真的从怀里掏出一个用麻线装订的小本本,用一截木炭,一脸崇拜地开始记录:“某年某月某日,土地爷王老根,设神罚之阵于一线天,坑杀逆贼无数,其声之惨,三日不绝……”
整个战场,彻底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追逐与屠杀。
崔明远在几个亲卫的拼死保护下,亡命飞奔。他不敢回头,他怕看到那如同修罗地狱般的景象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逃出这片魔鬼之地时,前方不远处的路口,几道黑影闪出,拦住了去路。
为首的,正是周通。他没有拿他那杆标志性的长枪,腰间别着一把造型精巧的短火铳,手里却拎着一根粗大的绳索,脸上带着一丝狞笑。
“崔公子,我家大人有请。这么着急走,是赶着回去投胎吗?”
“滚开!”崔明远的亲卫队长又惊又怒,他知道今天断无幸理,怒吼一声,拍马舞刀,打算拼死一搏,为公子杀出一条血路。
周通不闪不避,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嘲讽。他甚至没有拔出腰间那支象征着身份的短火铳。
就在那亲卫队长靠近的瞬间,周通身边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乡勇,猛地将手中的一大张渔网撒了出去。
那亲卫队长武艺不凡,反应极快,挥刀想将渔网砍破。可这渔网是用特制的麻绳浸油编织而成,又软又韧,一刀下去,非但没砍断,反而被缠住了刀刃。他再想发力,渔网已经当头罩下,瞬间就将他连人带刀裹了个严严实实。
战马受惊,人立而起,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不等他挣扎,几个早就准备好的乡勇已经一拥而上,绳子一捆,破布一塞,像拖死狗一样拖到了一边。
剩下的几个亲卫,吓得肝胆俱裂。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,周通已经动了。
他的速度快如猎豹,身影一闪就冲入人群。没有花哨的招式,一拳,一脚,一记手刀,招招都打在人最脆弱的关节和脖颈上。只听几声沉闷的哼声,剩下的几个亲卫,已经全部软倒在地,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
崔明远呆呆地看着这一幕,手中的长剑,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。他最后的倚仗,没了。
周通拎着绳子,一步步向他走来,脸上的笑容,在崔明远看来,比传说中的恶鬼还要可怕。
“你……你别过来!”崔明远色厉内荏地叫道,“我爹是崔振!冀州崔家的家主!你敢动我,我崔家,绝不会放过你们!”
“你们崔家,现在还有空管你吗?”周通嘿嘿一笑,手脚麻利地将这位不久前还不可一世的崔家嫡公子,捆成了个结结实实的粽子,随手扔在了地上,还顺便踢了一脚,“老实点,不然把你吊在城门楼子上,让你爹拿钱来赎。”
当沈轻雪带着城里最后一批组织的青壮,气喘吁吁地赶到一线天时,战斗,已经彻底结束了。
她被眼前的景象,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整个山谷,仿佛被血洗过一般。残破的旗帜,断裂的兵器,还有层层叠叠的尸体,铺满了狭窄的通道。空气中,弥漫着浓烈刺鼻的硝烟与血腥味,混杂着一些不可名状的秽物气味,熏得人几欲作呕。
那些刚刚还气势汹汹,号称要踏平青阳的崔家大军,此刻,要么变成了冰冷的尸体,要么就成了跪在地上,被乡勇们用各种武器看押着,瑟瑟发抖的俘虏。
而在山谷之上,那支黑色的军队,正沉默地列队站着。有些年轻的士兵,脸色苍白,正扶着墙壁在干呕,但他们的队列,依旧笔直如松。
陈默站在最高处,山风吹动着他的衣角,将他身上淡淡的硝烟味吹向远方。他的脸上,看不出打了胜仗的喜悦,也看不出面对尸山血海的悲伤,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。
沈轻雪的心,猛地一颤。
她看着那个男人,忽然感觉到了一丝陌生,和一丝……难以言喻的恐惧。
这才是他的真面目吗?那个平日里看起来有些懒散,喜欢在县衙后院喝茶,偶尔还会开几句无伤大雅玩笑的男人,一旦化身为战争之神,竟是如此的冷酷与决绝。
陈默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目光,转过头来,对她微微一笑。
那笑容,如同春风化雨,瞬间冲淡了他身上的肃杀之气,让他又变回了那个熟悉的陈默。
“沈大人,你来晚了,好戏已经散场了。”
沈轻雪张了张嘴,千言万语涌到喉头,最终只化为一句有些干涩的问话:“伤亡……如何?”
“神机营,无人阵亡,三人装填火药时操作失误,烧伤了手,皮外伤。”陈默的语气很平淡,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“乡勇这边,冲得太猛,死了二十七个,伤了五十多个。都是好样的。”
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正在打扫战场,收集战利品的乡勇,眼神里,终于多了一丝温度。
“把我们的英雄,好生收殓。他们的名字,要用最好的工匠,刻在英灵祠的第一排。”他又转向跑过来的周通,“至于战利品……崔家这次,可是给我们送了一份大礼啊。”
周通兴奋地搓着手,脸上全是喜色:“大人您放心!甲胄八百多副,都还是好的!长刀弓弩上千,还有马匹、粮草……咱们这下发了!足够再把神机营,扩充一倍!”
沈轻雪看着那些百姓,小心翼翼地从崔家士兵尸体上,剥下那些曾经让他们无比畏惧的铠甲,拿起那些锋利的武器,眼中没有贪婪,只有一种朴素的,改善生活的喜悦。
她忽然明白了。
这不是屠杀。
这是在一个即将崩坏的世道里,一群想活下去的人,用最原始,最血腥的方式,为自己,也为子孙后代,抢夺生存下去的权利。
而陈默,就是那个带领他们,抢夺这一切的人。
青阳县衙的大牢,迎来了有史以来最“尊贵”的客人。
崔明远被关在最深处的一间独立牢房里,没有刑具,地上甚至还铺着干净的稻草。但他身上的狼狈和眼神中的死寂,比任何酷刑都更折磨人。他败了,败得一塌糊涂,败得莫名其妙,败得让他怀疑人生。
“吱呀”一声,牢门被打开,陈默提着一个食盒,走了进来。
他将几样看起来还算精致的小菜和一壶温好的酒,摆在牢房中间那张矮小的桌上。
“崔公子,受惊了。尝尝我们青阳县的粗茶淡饭。”
崔明远猛地抬起头,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陈默:“要杀就杀,何必假惺惺!”
“杀你?”陈默笑了,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,放在鼻子下闻了闻,“崔公子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杀你,对我有什么好处?你的命,现在一文不值。但你活着,却还有点用处。”
崔明远攥紧了拳头,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。这种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羞辱,比死还难受。
陈默抿了口酒,似乎在品味,又似乎在组织语言,慢悠悠地开口:“你父亲崔振,倒算是个枭雄。二十年前,为了争夺家主之位,不惜与外敌勾结,亲手设计,害死了自己的亲大哥,也就是你的大伯,崔明德。对外,却宣称是暴病而亡。这件事,做得干净利落,连崔家的老太爷,都被蒙在鼓里。”
“轰!”
这句话,如同九天惊雷,在崔明远脑中炸响。他脸上的血色,瞬间褪得一干二净。他瞪大了眼睛,像是见了鬼一样看着陈默,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这是崔家最核心,最阴暗的秘密,除了他父亲和他这个继承人,绝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!
陈默没有理会他的震惊,继续用那种平淡的语气说道:“还有河间府的‘福运’盐场,明面上是属于知府大人的小舅子名下的产业,实际上,每年七成的利润,都悄悄流进了你们崔家的口袋。靠着贩卖私盐,你们崔家,这十年里,至少多赚了三十万两白银吧?这要是捅到朝廷那里,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”
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?!”崔明远的声音,因为极致的恐惧而剧烈地颤抖。
眼前的这个人,根本不是什么小小的县令!他仿佛有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,所有隐私,所有秘密,在他面前,都无所遁形。
“我是谁,不重要。”陈默又给他倒了一杯酒,推到他面前,“重要的是,崔公子,你现在想不想活下去?”
崔明远的心理防线,在这一刻,彻底崩溃了。他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世家公子,变成了一个被人捏住了无数致命把柄的阶下囚。他看着陈默,眼神里充满了畏惧和哀求。
“你想……让我做什么?”
“很简单。”陈默的脸上,露出了一个堪称和善的笑容,“当个信使,回家给你父亲,带封信,还有一份……我精心准备的礼物。”
---
青阳县的城门外,来了一队不速之客。
这队人马不多,约莫三十余骑,但气势却远非崔家的乌合之众可比。骑士个个身穿统一的玄色劲装,腰佩制式长刀,目光锐利,行动间自有一股肃杀之气。他们护卫着一辆黑色的马车,马车前,两杆大旗迎风招展,一杆上书斗大的“肃静”,另一杆则是“回避”,而最引人注目的,是队伍中央一面绣着金边獬豸的旗帜,旗下三个篆字——都察院。
都察院,纠劾百官,辨明冤枉,提督各道,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。
这三个字,在大周朝任何一个官员的耳朵里,都比阎王爷的催命符还管用。
王老根得到消息,第一时间就冲进了县衙后堂,陈默正在那里和周通、沈轻雪复盘战后的各项事宜。
“大人!不好了!京里来人了!”王老根扛着他的宝贝锄头,一脚门里一脚门外,嚷嚷得整个县衙都听得见,“打着那个什么‘都察院’的旗号,为首的是个官儿,看着比崔家那小子还难伺候!这帮家伙,鼻子比狗还灵,咱们这才刚打完仗,他们就闻着味儿来了!”
周通闻言,眉头一皱,手不自觉地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。沈轻雪的脸色也微微一变,都察院的钦差,这可比河间府的知府麻烦多了。这意味着,青阳县的事情,已经惊动了朝廷中枢。
陈默却笑了。他放下手中的账册,缓缓站起身,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,神情不见丝毫慌乱,反而有一种“终于来了”的释然。
“该来的,总会来的。”他看着城门的方向,眼神平静而深邃,“崔家在朝中经营多年,我们打了他的脸,他自然会找来更厉害的角色。走吧,去会会这位,从京城远道而来的……钦差大人。”
城门口,早已清出了一片空地。
陈默带着沈轻雪和周通,不卑不亢地站在那里。没有大张旗鼓地迎接,也没有畏畏缩缩地躲避。
马车停稳,车帘掀开,一个身穿绯色官袍,头戴乌纱,面容清瘦,颌下留着三缕长髯的中年官员,在两名护卫的搀扶下,缓缓走了下来。他约莫五十岁年纪,一双眼睛却不像他的年纪那般浑浊,反而锐利如鹰,扫视之间,带着一股审视的威严。
他目光掠过周围,最后落在陈默身上,开门见山地问道:“你就是青阳县令,陈默?”
声音不高,却自有一股居高临下的压力。
“下官陈默,见过钦差大人。”陈默拱手行礼,姿态放得很低,但腰杆却挺得笔直,“不知大人驾临,有失远迎,还望恕罪。”
那官员“嗯”了一声,不置可否,自我介绍道:“本官,都察院左佥都御史,魏征明。奉圣上口谕,前来冀州,查察河间府崔氏与青阳县械斗一案。陈大人,你可知罪?”
最后三个字,魏征明加重了语气,如同法官在宣判。
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周通的眼神一冷,向前踏了半步,却被陈默一个不着痕迹的眼神制止了。
陈默脸上依旧挂着那副从容的微笑:“下官愚钝。敢问大人,下官何罪之有?”
“何罪之有?”魏征明冷笑一声,声音陡然提高,“你一介县令,未经上报,擅自调动乡勇,与河间崔氏爆发大规模械斗,致使上千人死伤,血流成河!你聚众私斗,形同谋反,此其罪一!你治下县民,竟敢剥取士卒盔甲,此乃大不敬,其罪二!本官还听说,你私设工坊,打造兵器,招募乡勇,编练军阵,陈大人,你这是想在青阳县,当你的土皇帝吗?此其罪三!这三条罪,哪一条,不够你满门抄斩?”
魏征明的话,字字诛心,每一句都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重罪。他带来的护卫,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,气氛瞬间剑拔弩张。
沈轻雪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她没想到,对方一上来,就如此咄咄逼人,完全不给任何辩解的机会。
陈默却像是没听出话里的杀气,脸上的笑容反而更盛了。
“大人息怒。您远道而来,车马劳顿,不如先入城喝杯粗茶,歇歇脚。至于这几条罪名,下官相信,等大人亲眼看过如今的青阳县,自然会有公断。”
他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,态度谦恭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。
魏征明双眼微眯,深深地看了陈默一眼。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个惶恐不安,或是桀骜不驯的地方官,却没想到,是这么一个深不可测的年轻人。对方的镇定,让他心里生出了一丝异样。
“好,本官就看看,你这青阳县,到底被你打理成了什么模样。”魏征明拂袖,迈步入城。
他没有直接去县衙,而是提出要先看“战场”。
陈默欣然同意,亲自陪同。
一行人来到一线天,尽管战场已经被打扫过,但那被鲜血浸染成暗红色的土地,空气中尚未完全散尽的血腥味,以及山壁上密密麻麻的弹孔,依旧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场战斗的惨烈。
魏征明看着那些深嵌在岩石里的铅弹,用手摸了摸一个弹孔,脸色变得异常凝重。他行伍出身,自然看得出这绝非寻常弓弩所能造成的破坏力。
“这就是你打败崔家八百甲士的武器?”他回头问道。
“回大人,此物名为火铳,乃下官偶然间从一本古籍上看到的图纸,命工匠仿制而成。威力尚可,只是装填繁琐,远不及朝廷天兵的神弓利箭。”陈默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魏征明没说话,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威力尚可?能将铁甲打成筛子的武器,叫威力尚可?这陈默,要么是在刻意藏拙,要么就是他手上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
接着,魏征明又提出要看青阳县的府库和工坊。
陈默依旧是满口答应。
当魏征明看到府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,整整齐齐码放的布匹和药材时,他的眼神变了。他去过冀州许多比青阳富庶得多的县城,但没有一个县的府库,能有如此充盈。
而当他来到河边那座热火朝天的工坊区时,他彻底被震撼了。
巨大的水车,带动着沉重的锻锤,“哐当!哐当!”地反复捶打着烧红的铁胚,火星四溅。每一次捶打,都比十几个壮汉合力挥锤更有力,更精准。而在不远处,一座高大的钻石高炉正冒着青烟,工人们喊着号子,将一炉炙热的钢水,注入模具之中。
这里生产的,不仅仅是长刀和盔甲,还有大量的锄头、犁头等农具。整个工坊,井然有序,充满了蓬勃的生机。
“这些……都是你弄出来的?”魏征明指着那台水力锻锤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“让大人见笑了。青阳贫瘠,只能多想想办法,让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。”陈默笑道。
魏征明沉默了。他一路走来,看到的青阳县城,街道干净,百姓脸上虽然还带着菜色,但眼神里却有光,有希望。这和他想象中那个被战火摧残,民不聊生的“贼巢”,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他开始明白,事情,远比奏报上写的要复杂。
晚上,县衙后堂。
魏征明没有再提“审问”二字,而是让陈默屏退左右,单独谈话。
“陈默,本官现在不以钦差的身份,而是以一个大周臣子的身份问你。你,到底想做什么?”魏征明盯着陈默的眼睛。
“回大人的话,下官想做的,和大人一样。”陈默给他斟了一杯茶,“让这世道,好起来。让百姓,能活下去。”
“说得好听!”魏征明冷哼,“靠你这些杀人的利器,和这满城的兵甲吗?”
“大人,如果道理有用,崔家就不会带兵来屠我青阳。如果朝廷的法度有用,河间府的刘知府,就不会坐视崔家拥兵自重,贩卖私盐。”陈默抬起头,目光灼灼地迎上魏征明,“大人,这世道已经病了。对付豺狼,光靠道理是不够的,你得有比它更锋利的牙齿。”
说完,他从袖中取出一本册子,轻轻地放在了桌上,推到魏征明面前。
“这是下官偶然得到的一本账册,或许,对大人查案,有些用处。”
魏征明疑惑地拿起账册,翻开第一页,他的瞳孔就猛地一缩。
这本账册,记录的不是别的,正是过去五年里,“福运”盐场每一笔私盐的走向,以及流入崔家和河间知府刘大人府上的,每一笔分红。时间,地点,经手人,数目,记得清清楚楚,滴水不漏。
这已经不是证据了,这是一把能将整个河间府官场连根拔起的刀!
魏征明拿着账册的手,开始微微颤抖。他来青阳,是奉了朝中与崔家交好的大佬的命令,来给陈默定罪,敲山震虎。可现在,陈默却递给了他一个天大的功劳,一个足以让他官升一级,名震朝野的惊天大案。
他猛地抬起头,死死地盯着陈默。
这个年轻人,从他进城的那一刻起,每一步,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展示武力,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展示民生,让他明白青阳民心所向。最后,再抛出这个让他无法拒绝的诱饵。
这不是一个莽夫,这是一个心机深沉,手段狠辣的政治怪物!
陈默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,端起茶杯,轻轻吹了吹热气。
“大人,崔家之恶,罄竹难书。青阳一战,不过是官逼民反。下官身为一县父母,为保阖城百姓性命,被迫自卫,情有可原。但崔家勾结地方大员,侵吞国帑,私贩官盐,此乃动摇国本的大罪,罪不容诛。孰轻孰重,相信大人心中,自有一杆秤。”
魏征明看着手中的账册,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笑容和煦的年轻人,后背,竟渗出了一层冷汗。
他知道,从他接过这本账册开始,这趟浑水,他已经不由自主地蹚进去了。而且,是站在陈默这边。
---
夜深了,县衙为钦差一行安排的院落里,灯火通明。
魏征明独自坐在书案前,那本薄薄的账册,此刻却仿佛有千斤之重,压在他的心头。他已经来回翻看了三遍,每一个字,每一个数字,都像烙铁一样,烫在他的脑子里。
他不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。在都察院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年,他见过的阴私龌龊,比寻常人一辈子吃的盐都多。他很清楚,这本账册意味着什么。
意味着一场官场大地震。
意味着他只要将这东西呈上去,河间知府刘承,以及他背后盘根错杂的利益集团,都将万劫不复。而崔家,这个在冀州盘踞百年的地头蛇,也将被彻底打断脊梁。
这功劳,太大了。大到足以让他忘记自己来青阳的初衷。
来之前,京中的那位尚书大人,曾隐晦地提点过他,青阳县令陈默,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莽夫,动了不该动的人,需要“敲打敲打”,让他知道朝廷的规矩。
可现在看来,谁敲打谁,还不一定。
那个叫陈默的年轻人,根本不是莽夫,他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猛虎。他给你看他锋利的爪牙,让你不敢动他。他给你看他治理下安居乐业的羊群,让你不忍动他。最后,他还给你指了一片更肥沃的草场,上面有一群更肥美的肥羊,让你不愿动他。
威逼,利诱,阳谋,阴谋。一套组合拳下来,自己这个所谓的钦差,已经完全落入了他的节奏。
“大人。”门外传来亲信护卫的声音,“夜深了,您该歇息了。”
“进来。”魏征明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
亲信护卫推门而入,手中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参汤。
“大人,这是县衙送来的,说是给您安神的。”
魏征明看了一眼那碗参汤,没有喝,反而问道:“白天让你去城里转转,有什么发现?”
护卫躬身道:“回大人,属下转了一天。这青阳县,确实邪门。城里的百姓,提起那位陈大人,那神情……不像是敬畏,倒像是信奉神明。属下还特意去了趟城隍庙,您猜怎么着?”
“怎么?”
“城隍庙里,除了城隍爷,居然还多了一尊神像,叫什么‘青阳府君’。那神像的面目,雕得跟陈大人有七八分像!”护卫压低了声音,脸上满是不可思议,“而且香火鼎盛,比城隍爷还旺!”
“生人立祠,私塑神像?”魏征明的手指在桌上有节奏地敲击着,眼神愈发深邃,“他这是要……封神啊。”
一个能打仗,会治理,懂权谋,还深谙蛊惑人心之道的县令。
魏征明忽然觉得,崔家惹上的,可能不是一个麻烦,而是一个能颠覆整个冀州格局的时代浪潮。而自己,正站在浪潮的最前端。
是顺势而为,还是逆流而上?
他看着那本账册,心中渐渐有了决断。
第二天一早,魏征明再次召见了陈默。
这一次,会面的地点,就在那座新落成的水泥工坊旁。巨大的水轮缓缓转动,带动着锻锤发出富有节奏的轰鸣,仿佛是这片土地强有力的心跳。
魏征明没有再提任何罪名,他的态度,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。
“陈大人,昨日看了你的火铳,今日又见了这水力锻锤,本官心中,感慨良多。”魏征明抚着长须,望着那不知疲倦的机械,“此等利器,若能用于边军,何愁北地胡虏不灭?此等巧思,若能推行天下,何愁大周不兴?”
陈默微微一笑:“大人谬赞。下官不过是拾人牙慧,侥幸成功罢了。”
“不必过谦。”魏征明摆了摆手,话锋一转,声音压低了几分,“陈大人,本官问你,你这火铳,一月可得多少杆?这精钢,一月可炼多少斤?”
他不再是审判者,而变成了一个考察者,一个评估者。
陈默心中了然,知道对方已经做出了选择。
“回大人,火铳制作工艺复杂,良品率不高,一月不过百杆。精钢冶炼,受限于焦炭和铁矿,一月也仅得数千斤。青阳一地,终究是底子太薄。”陈默半真半假地诉苦。
魏征明点了点头,这和他预估的差不多。这等逆天之物,如果还能大规模量产,那陈默就不是猛虎,而是真龙了。
“本官此番回京,会如实上奏。”魏征明看着陈默,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河间崔氏,拥兵自重,鱼肉乡里,形同叛乱。青阳县令陈默,为保境安民,率地方军民奋起反抗,平定叛乱,此乃大功一件。至于私造兵器一事,乃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,其心可悯,其情可原。”
这是在给他定性了。
陈默拱手:“多谢大人体恤下官苦衷。”
“但是,”魏征明话锋再转,眼神变得锐利,“崔家私盐一案,关系重大,必须彻查。本官需要人证物证,需要一个能打开河间府局面的……引子。”
“大人放心。”陈默心领神会,“下官的神机营统领周通,对河间府地界颇为熟悉,可带一队人马,‘协助’大人办案。另外,崔家嫡子崔明远,如今就在青阳大牢里,他知道的东西,想必比账册上更多。”
“好!”魏征明抚掌大笑,心中的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。
陈默不仅给了他刀,还把磨刀石和握刀的手法,一并奉上。有了崔明远这个污点证人,再加上周通那些“不走寻常路”的手段,撬开河间府那些官员的嘴,易如反掌。
一场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,就在这轰鸣的工坊旁,达成了。
三日后,钦差魏征明一行,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青阳县,直奔河间府城而去。与来时不同,他的队伍里,多了五十名穿着崔家甲胄,气息彪悍的神机营士兵,带队的,正是周通。而队伍的囚车里,关押的则是面如死灰的崔明远。
送走了魏征明,沈轻雪站在城楼上,看着远去的队伍,依旧觉得有些不真实。
“就这么……解决了?”她看向身旁的陈默,眼神里满是复杂,“一场足以让青阳万劫不复的滔天大祸,就被你用一本账册,三言两语,化解于无形,甚至还让他成了我们的助力。”
“这不是化解,是转移。”陈默看着远方,淡淡地说,“对付饿狼最好的办法,不是跟它拼命,而是告诉它,东边的山坡上,有一群更肥的羊。只要我们跑得比羊快,狼就不会回头来吃我们。”
沈轻雪似懂非懂,但她看着陈默的侧脸,心中那丝因杀戮而起的恐惧,已经彻底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敬佩所取代。这个男人,拥有的不仅仅是神鬼莫测的武器,更有洞悉人心的智慧。
半个月后,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河间府传来,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冀州。
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魏征明,以雷霆之势,查抄了河间崔氏,封禁了“福运”盐场。河间知府刘承,以及下属十余名官员,被当场革职,打入大牢。从崔家和刘知府家中,抄出的金银财宝,据说堆满了整个府衙的院子。
冀州官场,人人自危。
而就在这风口浪尖上,一队车马,低调地从河间府来到了青阳县。
为首的管家,见到了陈默,二话不说,纳头便拜,并呈上了一份礼单和一封信。
信,是崔家如今的掌舵人,崔振亲笔所书。信中言辞恳切,极尽卑微,称自己教子无方,冒犯天威,罪该万死。为求赎罪,特献上白银十万两,粮食五千石,另有各种珍稀药材、布匹绸缎,装满了整整五十辆大车。只求陈默能高抬贵手,放过崔家剩下的一点血脉。
他怕了。
被陈默的雷霆手段和政治手腕,彻底打怕了。他宁愿倾家荡产,也要换取那个怪物的……原谅。
陈默收下了礼物,看着那封信,随手扔进了火盆。
他站在县衙的最高处,俯瞰着下方这个已经脱胎换骨的县城。工坊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,学堂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,操场上,扩编到八百人的神机营,正在进行队列操练,口号声震天动地。
一线天立威,都察院破局。
他一手染血,一手执棋,终于在这崩坏的世道里,为自己,也为这满城百姓,打下了一片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棋盘,已经摆好。
“沈大人,”他忽然开口,对身旁的沈轻雪说道,“通知工坊,我们的高炉,可以再建两座了。神机营,也可以再扩充一个炮兵营。”
沈轻雪一愣:“还要扩军?我们……又要打仗了吗?”
陈默摇了摇头,目光越过青阳的城墙,望向了更遥远的,冀州乃至整个天下的方向。
“不。”
“是时候,让别人,来跟我们谈规矩了。”
《杀人减功德这仙还修个锤子:结局+番外》资讯列表:
为您推荐

 >
> 出国七年回来,发现妹妹换人了余平悦泽森无删减+无广告
出国七年回来,发现妹妹换人了余平悦泽森无删减+无广告 假千金死后,他们都后悔了林云舟林沫后续+完结
假千金死后,他们都后悔了林云舟林沫后续+完结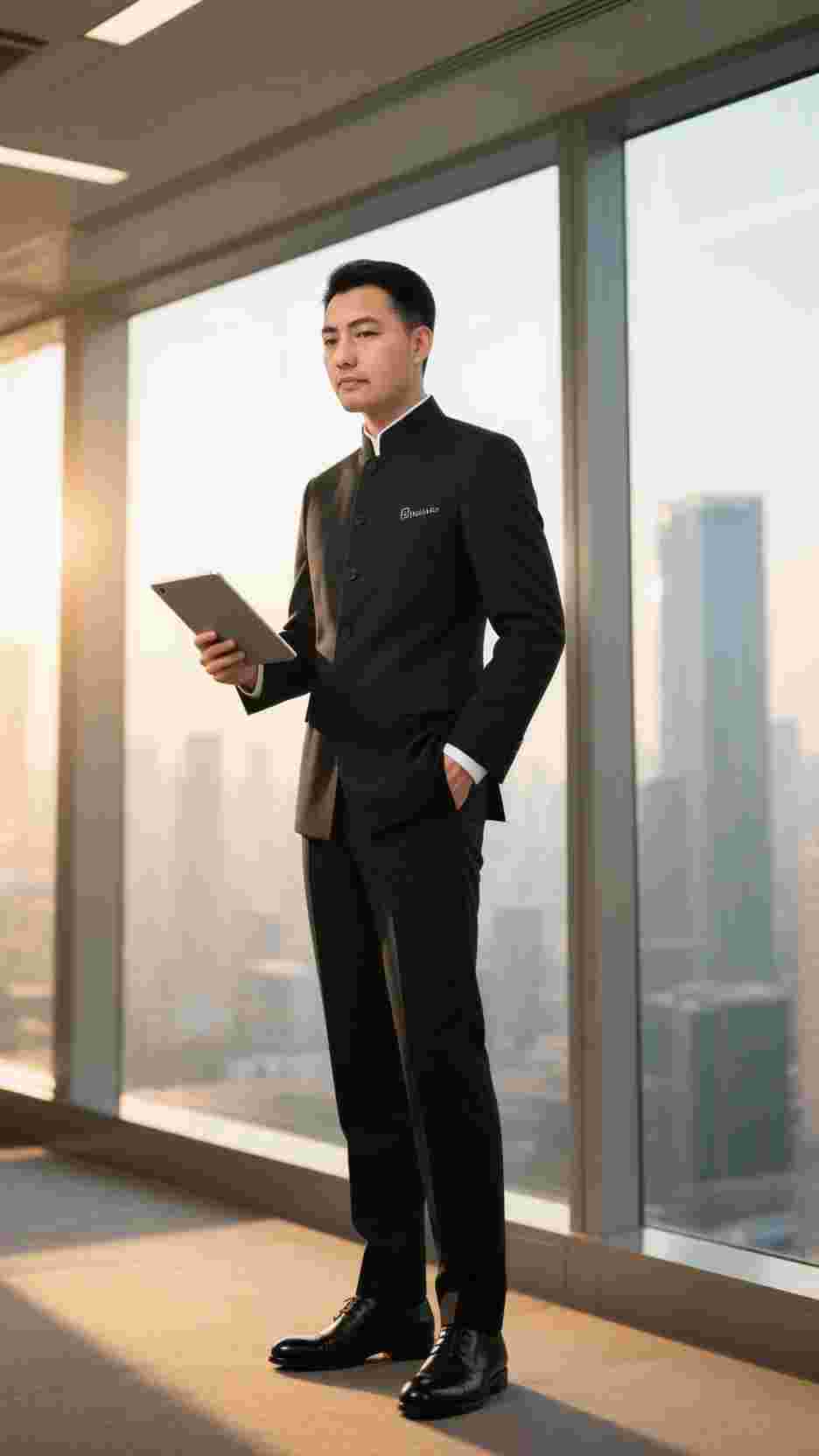 假千金死后,他们都后悔了林云舟林沫:全章+后续
假千金死后,他们都后悔了林云舟林沫:全章+后续 假千金死后,他们都后悔了全本+番外+后续
假千金死后,他们都后悔了全本+番外+后续 丈夫把我私人岛屿送给新欢,我让他身败名裂季墨尘林薇薇全文免费
丈夫把我私人岛屿送给新欢,我让他身败名裂季墨尘林薇薇全文免费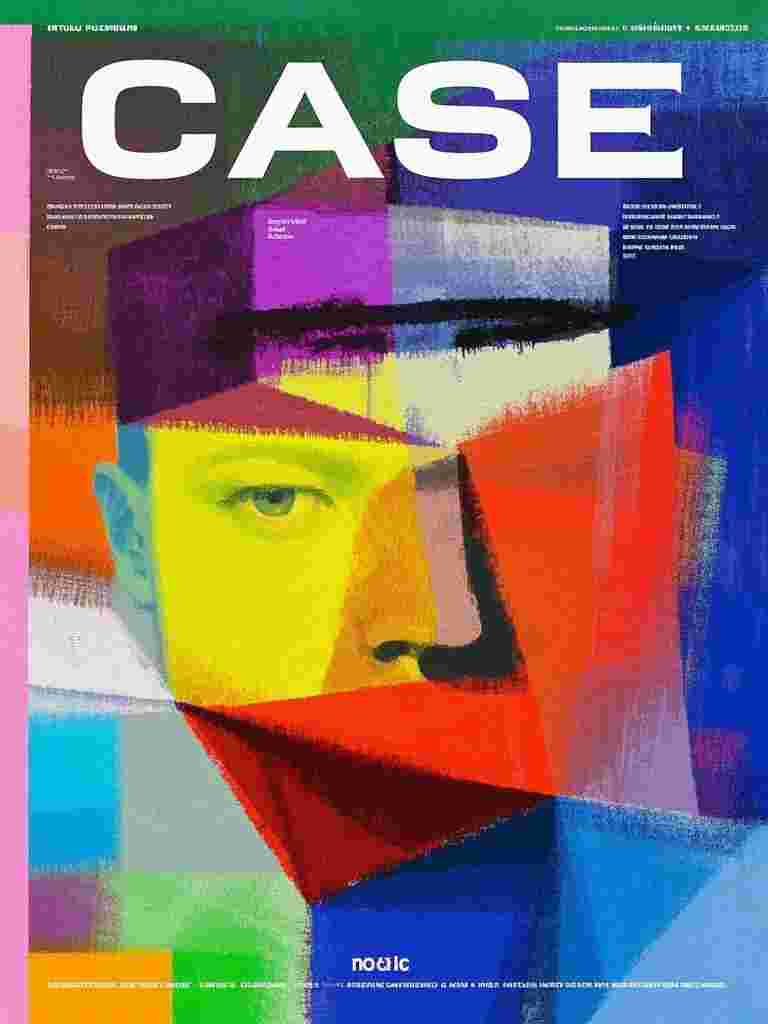 丈夫把我私人岛屿送给新欢,我让他身败名裂
丈夫把我私人岛屿送给新欢,我让他身败名裂 孙子政审因我坐过牢未通过,可我的罪名是通共啊许丽陈明全局
孙子政审因我坐过牢未通过,可我的罪名是通共啊许丽陈明全局 孙子政审因我坐过牢未通过,可我的罪名是通共啊许丽陈明全文
孙子政审因我坐过牢未通过,可我的罪名是通共啊许丽陈明全文 孙子政审因我坐过牢未通过,可我的罪名是通共啊许丽陈明番外+无删减版
孙子政审因我坐过牢未通过,可我的罪名是通共啊许丽陈明番外+无删减版 未婚夫把手捧花换成骨灰盒,我改嫁他悔疯乐乐姜思雅无删减+无广告
未婚夫把手捧花换成骨灰盒,我改嫁他悔疯乐乐姜思雅无删减+无广告